江南忆,常忆是杭州
江南忆,常忆是杭州
——回忆我的老师和同学
电真空器件75届 晏放成
看了题目,细心的朋友要我说道说道:何以要将白老先生的“最”改而为“常”。我的回答很简单:白居易忆的是景,老晏忆的是情。因为这里有我的母校,我的同学,我的老师。有说来细小实则珍贵,看似平凡实则难忘的记忆。那是深藏心底的情怀;是并不如烟的往事;是不可复制的岁月;是弥足珍贵的人生。所以,对于杭州,我怎能不——或者说只能是——常忆复长忆呀。
那么,我可以回忆了……

对于父母的早故,王德苗老师至今耿耿于怀。子欲养而亲不在,在和王老师的接触中,我们时不时地感觉到,这无法弥补的遗憾,成了他终生的痛楚。我想说的是,在这物欲横流,传统美德似乎已经一钱不值的年代,能把远去的老人记在心上,并且一记就是四十多个年头,这样的儿子,实在是难得一见了。那么,我不相信,人一走,果真就一了百了。我只相信,两位老人家,一定在天堂的某个角落,注视着王老师,牵挂着王老师;我只相信,他们定会在另一个世界,用他们那颗质朴、善良、兹爱之心,陪伴王老师走完剩下的人生之路。
平时,王老师就象我们的兄长,这并非空口说白话,有例为证:当他得知某同学病重后,发微信给在杭的同学(复述不免走样,原文照抄):“他治疗的事拜托各位了,他老婆又要带小孩,又要做家务,里里外外一个人忙得实在没有多少时间来看顾他,只有他妹妹在照料他,我看了很揪心,以后有谁去看他的时候记得叫上我。”
每次同学集会,总是王老师张罗,听说10月23日至25日,我们班又要召集毕业四十年同学会,早在9月份他就忙前忙后,比我们还上心。不巧的是他21至23日在成都有个研讨会,并有他的主题报告,他没法不去。只能临行又给同学们的手机发信息交待说(依旧原文照抄): “二十三日会议一结束我会立即赶晚上的飞机回杭和大家见面。行前几件事要交待一下。一、24日早上8点徐国良书记的报告已再次确认。二、你们这几天(指在杭的同学)如果要去看117会议室,可找109室的陈波同学(王老师现在的学生)。三、117会议室要用校园卡开,你们去找我的研究生开门。四、会议室的开水我现在带的研究生会准备好。五、24日的中餐已预定好,地点在浙大北门附近的留学生餐厅,11点开饭。”
“11点开饭。”
“真细致!”我感叹。
“真周全!”尹同学说。
其实,我们都错了,这岂是细致周全这么简单。王老师是将他的爱、他的情、他的人生信条贯彻到了生活中每一个角落的人。

这次我因故未参加,记得三十周年集会上,季敬川老师随口就叫出了每个同学的名字,要知这是时隔三十年;要知这是他教过的所有班级中的其中的一个班;要知道季老师已是八十多岁高令的老人。
“季老师的记忆真是惊人啊!”同学们不由得这样惊叹。
然而,果真仅仅是记忆力的问题么?
我想起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一个小故事:据说他在担任财长的时候,别人提问,他随口就能说出你要的一连串数据,且准确无误。同仁们说:田中,你简直是个记数字的鬼才啊。
田中微微一笑说:这并不难,在大街上你偶遇一个心仪的女子,很容易就能将她的容貌记下来,记数字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相信,季老师能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每回见到周文老师,我总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不是因为他那槐伟的身材;也不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而是因为他的风范、他的智慧、他的见解、他的严峻。我不是要在这里来评议先生的为人(我哪有这个资格)。而是每每见到周老师,就会有一种敬畏感,就会让我想到很多很多。比如我们班三十周年集会时周老师发言中的一段话:“据说现今社会上有个很精彩的说法,说是北大做官的多,浙大做学问的多,这种说法有多少准确度我们不管它,我要说的是,做官很大程度上是机遇的成份居多,而做学问却要耐得住一生的寂寞。”这是个看似随意,实则要往深里想想的问题。
而让我感到敬畏的,则是他的严峻,记得毕业三十周年集会时,弄了个录像片,我为其配了个解说词,想请他雅正。记得周老师看后,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淡淡地说了六个字:“多读读迅翁吧。”
我知道,他不点头,显然是我的文学素养离他的期望值还相差太远,而不摇头,或许是觉得我还有点孺子可教的意思在罢,而鲁迅先生的道德文章,岂是我所能望其项背啊!

真没想到,几年不见,王厚让同学竟有如此的成就,在同学们的言谈中我才知道,那幅字竟然出自王厚让之手,可惜他的文章我打不开,还没有读拜,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出会是怎样的大手笔。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了解王厚让这个人,知道他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是呀,这年头,要没有点宁静淡泊的心境;没有点通达宽厚的操守,要潜心于书法艺术,要安坐于文堂书斋,怕是万万不能的。
那年上北京办事,说好住刘艳单位招待所,大冬天,火车到北京已是晚上10点多,刘艳怕我找不到具体地方,只得冒着凛冽的寒风,一个人站在德胜门外大街的辅路上死等。看得和我一起出差的同事都唏嘘不已。
这个晚上,这个晚上的北京,让我感受到的仿佛不是北风的无比凛冽,而是雪花的无限美丽。
第二天约北京的几位同学集一集,雨雪中,老马和老尹骑着个破破旧旧的自行车,穿着那种传统的雨衣,哐当哐当地来了,要知道,北京可是一个大得让人感到累的城市啊,他们进来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了,也不知道是雨水呢还是汗水。
同学做到这个份上,还需要再说些什么吗?
听楼新民说,有一次为安排这次同学会的一个议题,李利华倒了三次车赶到学校。筹划同学会的过程中,他常常为一些很锁碎的事情不断地和大家联系,微信说不清就用语音,语音不行就视频,视频再不行就干脆用电话,记得有一次为这次同学会关于摄像的事,她在电话跟我说了太约半个小时之久。我一边接电话,一边想,这很像是某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为单位的一次活动作精心的安排和操劳。所不同的是,办公室主任是受领导的指派,而她,却是出自与生俱来的热忱。海天时不时地会发一些杭州的景观照到群里,比如杭州的音乐喷泉、杭州的夜色等等,好象是说,杭州这么美,欢迎大家多来看看。是的,我们是要来的,不过不是为了杭州的山水,而是因为杭州城里有比山水更美的风景——zd802。

成融荣瞒着自己的病情,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的病情,令大家多了一份牵挂,一份忧伤;而师生们的情谊,则令他多了一份慰藉、一份温暖。我虽然不在场,但我可以想象,当他坐着轮椅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当时该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瞬间!

这让我想起那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十几年前,历经磨难,身患绝症,挣扎在生活底层的普通农民胡国和,无意间听到了湖北楚天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江霞朗诵的女诗人胡鸿的诗:“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路上的人呵,你们累不累。以后的岁月,还得苦苦奋斗,风里雨里,你要好好的走。”这些句子真切地打动了他,于是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退伍军人提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愿望:想见见女诗人,想听听江霞的亲口朗诵。
这事感动了胡鸿和江霞。于是,汉口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们打开专门为这位农民兄弟特制的诗歌磁带,伴随着萨克斯哀婉的《回家》的音乐:“风里雨里,你要好好的走……”《中国青年报》曾以《美丽的忧伤》为题刊发长篇通讯,记录了这个感人的场面。
我们不是诗人,无法为成同学写出荡气回肠的诗句,我们也不是播音员,无法用甜美的嗓音唤回他昔日的风采。但我们会用行动为他寻找康复的途径和办法;我们会用真情在遥远的地方为他祈祷奇迹的出现。
让我们带着一份永远挥之不去的牵挂,永远记住这个秋天,记住浙大117室,记住2015年10月24日这个美丽而忧伤的上午。
楼新民,终于说到楼新民了。对于老楼,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当我真的面对楼新民这三个字的时候,感觉反倒是无话可说,一番思忖后还是觉得无话可说。要知,此时无声胜有声,还是说句大实话吧:这个人,与他相遇,是你的喜气;与他相交,是你的运气;与他同学,是你的福气。真的,我相信,凡接触过楼新民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面对他,本来烦躁的心突然会安静下来。他会让你一下子看清了世界、看清了人生、看清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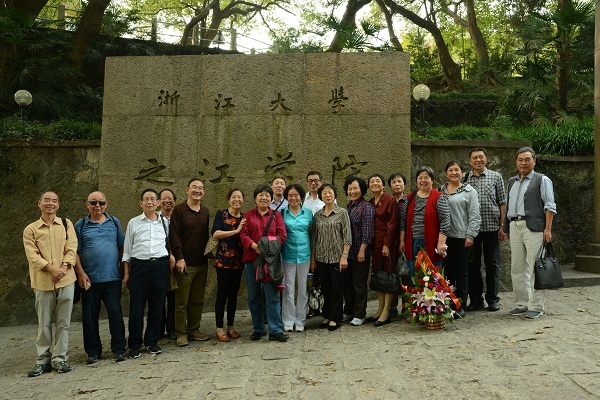
文章已是太长,周班长这篇大文章只能留待下一回了。其实,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要写出来,谁不是一篇绵秀文章啊,比如:朱坚红的善解人意,张美琴的亲切仁爱,老马的与时俱进,朱菊新的清纯无遐,杨利民的平实智慧,老头子的宽厚随和,王峰的深思熟虑,李玉华的心直口快,谭连顺的风趣幽默,席金秀的含蓄矜持,谢淑媛的落落大方,章绍东的随遇而安,杨德贵的沉静平稳,杜利放的温文尔雅,徐银梅的热情奔放,田美风的细致朴实,万道田的淳厚善良,张苏贞的心淡如水,赖大安的雷厉风行,王素琴的简约凝重,汪哲中的大智若愚,张明勋的山高海深等等等等,篇幅有限不能都展开来说了。
至于我自己,真是惭愧得很,至今还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唯一感到自慰的是没有沾上时下流行的“贪”字,所以虽身在容易犯错误的部门,却也能像同学们一样平平安安的安享晚年。
总之,我们的这些同学和老师,按时髦的说法,是正能量;按传统的说法,是大好人。
想到在天南海北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我认定,这个人间,还有一线希望,这个世界,还有一线希望。
